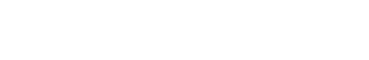薄荷暑记
八月暑夏,蝉鸣把槐树叶子晒得卷边时,我正在书房整理旧书。书房中昏沉的光线里浮着细小的尘埃,混着老木头与旧纸张的淡香。我的指尖拂过积灰的《昆虫记》,硬壳封面上法布尔手绘的甲虫还清晰可见,只是书脊处已有些褪色。稍稍翻开,牢牢停在其中折了角的一页,便见一片夹了很久的薄荷叶,突然就想起去年曾答应过爷爷要给他种一盆薄荷。
清晨五点的菜市场总飘着露水味。我蹲在摊前挑薄荷苗,卖花的婆婆用蒲扇拍着我的后背道:“选带绒毛的,好养活。”竹篮里的薄荷蹭着我的手腕,凉丝丝的气息混着早点摊的油条香不自觉地漫上来。爷爷看我买了薄荷回来,立刻在阳台上腾出块地方,然后把一个旧陶瓷盆洗得发亮,并教我把土壤攥成能散开的团,这才说:“得让根能透气,就像人要开窗通风一样。”我一边笑着答应,一边小心地把薄荷种好。
之后,浇水成了我的日常功课。当晨光斜斜切过窗台时,我举起小水壶绕着花盆转圈,看水珠顺着薄荷锯齿状的小叶子滴到土里。一天,我发现叶尖发焦,急忙跑去问爷爷,他指着盆底的小孔笑:“这是水多了烂根。”后来,我学会把手指插进土里估摸干湿,爷爷说这叫和薄荷“聊天”。
薄荷长得很快,没过多久就爆出盆沿。爷爷摘了几片泡在凉茶里,玻璃杯里浮着碎绿的影子,喝起来像含着片清凉的冰。
有一次,暴雨打歪了枝条,我蹲在雨里扶了半天,裤脚全湿透了。爷爷一边递来毛巾,一边指着重新挺直的茎秆:“你看,植物比我们想的坚强。”
八月末整理阳台时,薄荷叶已能盖住整个花盆。我剪了些枝叶分给邻居。爷爷用薄荷叶腌了糖醋黄瓜,还送给邻居一小碟。傍晚坐在藤椅上,薄荷香飘散在晚风里,远处的蝉鸣好像也软了些。
现在陶瓷盆里的薄荷还在长,我却要回学校了。清晨路过阳台,总看见爷爷在给它浇水,背影和晨光叠在一起,像幅安静的画。
这个暑假,我没去远方,却在一方小小的花盆里,读懂了生长的秘密。原来耐心等待一株植物抽枝展叶,和等待自己慢慢长大,是同样温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