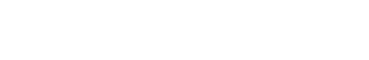雪落成诗
十二月的北国总归是该飘落几片雪的。冬日早晨漫步雪地,满目雪白,寒意随雪白浸染开来,冷冽入骨,与三五好友聊天时,望着手心落下的那转瞬即逝的雪花,我总会想起高三那年的那一场雪,似乎已在记忆中飘了不知几个三百六十五天了。
南方的孩子对雪是不熟悉的,似乎那片片晶莹白皙的雪花只存在于儿时的电视机,它更像一个形容词,代表着纯粹的冷,却无关真实的触感。所以,当那一片、两片,继而千片万片的莹白从铅灰的天幕深处飘落时,往日沉闷的高三教室,宛如被投进石子的深潭,漾开一片近乎狂喜的涟漪。
卷角的习题集被合上了,笔也被匆匆搁在一旁,一双双因埋头苦读而疲惫的眼眸此刻也被窗外那片明亮的雪白点亮了。不知是谁第一个推开了门,冷冽的朔风伴着雪花涌入沉闷的教室,随之涌出的,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少年,就连老师也笑着无奈地向我们摆摆手,于是更多人跟随,我们是初入深海的游鱼,在皑皑刺眼的雪地里溅起一串欢腾的浪,那一刻,高三的矜持与安静被抛之脑后,我们也只是一群恣意玩耍的少年。
用手捧起雪花,掌心传来真实而冰凉的触感;仰头,任凭晶莹的雪花静静落在冻得发红的脸上,转瞬即逝,留下一点冰凉的湿润。几颗雪球在空中飞速掠过,击打在棉服上绽放成一朵朵白色的花,我们肆意地笑着,仿佛这片雪白的世界早已属于我们。有人试着堆起一个不成形的雪人,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落叶与枯枝,点缀成眼睛与鼻子,即便手冻得发红,也无比专注地塑造着这注定转瞬即逝的歪歪扭扭的作品。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一切过于美好的创造,大抵都如这雪人一般,带着转瞬即逝的遗憾。
雪化得很快,在午后,这片雪白便所剩无几,那片欢腾的浪潮,此刻仿佛也随着雪的消逝而慢慢退去。我们又回到了那方有些闷热的教室,耳畔又传来熟悉的讲课声与写字声,玻璃窗上又重新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雾。我抬手轻轻拭去那片朦胧,望向窗外,残雪如星星般缀在草地上,倒显得有些不真实了。雪停了,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有一部分永远留在那片短暂的雪地中了,留在了那个雪天那场不顾一切的撒欢之中。
后来我到了北方,去了很多地方,似乎见到雪更容易了。北方的雪下的更加浩大,我却再没见到那一日的雀跃了:那日的雪,白得近乎刺眼,穿透了我那段灰蒙蒙的青春,在往后的无数次困顿与失意中,那雪仍会落在我的眉睫,提醒着我:我也曾那样真切地、鲜活地活过,也曾为了一片纯粹的白而欢呼雀跃过。
雪依旧下着,似有掩埋所有踪迹的架势,可总有些东西是掩盖不了的,就像此刻我心头飘落的那片带着温热的雪花。那日的雪从未真正停歇——那片片晶莹的雪花,在我回忆的原野上,静静闪着别样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