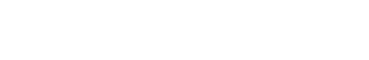蔷薇记事
华电路的转角处,野蔷薇开了满墙,像是一场盛大的欢宴,来告诉我们如何度过这样的五月。看到那些细嫩花朵在还未停下的风中摇曳生姿,浓绿的能掐出水的密叶衬着花瓣柔软的粉白,眼眸流转间,思绪又飘回了三年前的夏天。
图书馆斑驳的墙上,蔷薇烂漫之时,十七岁的我们总爱偷偷地把课桌挪到靠窗的位置。在某个闲散的午后,偏过头去仔细凝望,能感觉暮春的雨气还沾在花瓣上,初夏的日光已经蒸出某种清甜的气息。这种甜并不似桂花般浓烈袭人,倒像是哪个捣蛋鬼,悄悄把整盒彩色的染料碾碎了,撒在风里。
图书馆的管理员,六十岁的张叔说这堵花墙是九七届学长种的。他总爱操一口楚州口音的淮安话与我们谈天,“你们小女孩呀,就该和蔷薇拍照”,话没说完,我们就把借来的书放到台子上,咯咯笑着跑远了,因此也看不见他那皲裂得如同树皮般的皱纹里,藏着的爱惜。我和伙伴们一起细细数着花瓣上深浅不一的纹路,想起生物老师说的染色体联会。这些野蔷薇开得毫无章法,凭着一腔心意就恣意地舒展开来,倒像十七岁该有的样子。
体育课后,总有人躲在花荫里偷喝汽水。易拉罐开启的瞬间,气泡声惊起三两只栖息的蝴蝶。小林的帆布鞋永远沾着尘土,她立誓要收集七种颜色的花瓣做最独一无二的书签。我们笑她矫情,一年后却也都不约而同地在我们的毕业册里夹进干枯的蔷薇——原来,“青春”是种慢性病,潜伏在每根毛细血管里,在多年后的某个时刻翻开旧书时,才会突然发作,将你席卷。
黄昏总是比白日漫长些。值日生擦黑板时,粉笔灰混着斜阳在空气里游荡。我和小曼蹲在花墙根儿分食晚饭后自己偷偷带来的“加餐”——红豆面包和椰蓉酥,饶有兴致地看工蚁列队搬运掉落的花瓣。她说要考有海的城市,眼里有光芒闪烁,我盯着我们校服外套的第三颗纽扣,突然发现野蔷薇的刺,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生长。
教导主任突然出现在走廊拐角时,我们慌忙把面包袋塞进衣兜。他皮鞋碾过的地方,有朵完整的蔷薇正往下掉,花瓣边缘卷曲,仿佛是一张褪色的信笺。后来我在某个播客中听到,植物的趋光性会让它们永远追着太阳走,就像十八岁的我们相信明天一定会比此刻更明媚。
毕业后的校友群会时不时弹出消息,如随着学校领导层的换届,高三学生的学习节奏会有所变化,闲暇空间会被挤压。在那些传出的照片里,花墙依旧如故,只不过再没有那些鲜活的身影和清脆的笑声了。小曼从青岛寄来的明信片躺在信箱的最上层,在背面印着的浪花里,我隐约瞥见那年夏天曾许下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