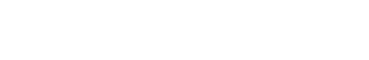华电故事
离家白日梦
发布时间:2014-12-26
供稿单位 :新闻中心记者团
作者:文/刘晓舒
我从小就很向往大山。那些密不透风的树叶,那些层层叠叠的草丛,那些被溪水柔和了的刺眼的阳光,那些荡悠在蓝天上的鸟儿,那些重峦叠嶂、层层叠叠的山峰……
小时候每次躺在爸爸杂货店里那张小沙发上,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这样的情景,可没做白日梦多久,睁开眼就是一个陌生人操着不同的口音问道:“小家伙,你爸爸呢?”于是接下来便是一如既往的忙碌和嘈杂。面目呆滞的行人来来往往,破破烂烂的车辆胡乱摆放,臭气熏天的垃圾随处可见,到处挥发着灰色的蒙眬尘埃和擦身而过油腻腻的汗味,这里是中国第一大压抑的农贸市场。我在这个农贸市场不知生活了多少年,吸了不计其数的尼古丁以及廉价的香水,喝了数不胜数的过滤糟糕的河水,染了毫不嫌多的头发颜色,泡了数量庞多的女人,于是乎我成为了父亲的痛苦根源,街坊邻居视为反面教材的“败类”。
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跑到音像店蹭音乐,带上我的小女朋友,一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边摇头晃脑,完了我问她:“好听吗?”
她干脆地甩了我一巴掌:“我们俩分手!”
最后我看着她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十步一回头,知道再也不回头的纤瘦的倩影,心想我真的是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的我买了把吉他开始玩音乐,想学着崔健玩摇滚当明星,最终真的一无所有。
父亲彻底没辙,他看着我鼻青脸肿地出现在他面前说被人骗去当明星拿不出一分钱时,沉吟了一会儿,说:“孩子,我允许你离家出走十年。”
我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十年之后,记得回来。”他淡淡地说完话,如往常一般走回房间,不着痕迹地没让我看出他在拭去眼角的泪水。
第二天,我背上自己的吉他和压岁钱,第一次离开了这个农贸市场。我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无尽的田野,麦苗们长起来浩浩荡荡的一大片,没有边际也没有方向,我好像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员,至少我现在就没有方向。
但是,我深知从小的梦想,我要走进大山,归于自然。
最后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一座偏远的小城,腹中无物的饥饿感我是第一次尝到。我摸遍了全身上下的口袋,悲哀地发现一分钱都没有,这才意识到我在火车上熟睡时被人偷光了钱,只剩下一把吉他,静静地用冰凉的触感提醒我如今窘困的境地。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抬头看到天上数不尽的星星一闪一闪对我笑,我也想对它笑,可是我笑不出来。我摸出口袋里一包从家里顺来的饼干,坐在天桥底下一口一口啃着竟然啃出了眼泪。旁边一个乞丐用他脏兮兮的脚踹了我一下,嘴里咕哝里:“新来的到一边儿凉快去,别妨碍大爷我睡觉。”我乖乖地坐到一边,靠着吉他睡着了。
一大早,那乞丐大爷继续用他脏兮兮的脚踹我:“新来的,吃早饭不?”
我惊醒过来,看到一张放大的布满皱纹的脸,眯眼笑着的样子像个捏好的包子:“吃不吃啊?”
我连忙答:“吃、吃。”
他扔给我一个脏馒头,上面被咬了几口,我擦了擦就狼吞虎咽起来,一边吃一边斜眼打量他。
这老头大约五十多岁,身上套着一件颇为考究却又脏到不行的黑色西装,套脚的蓝色校服裤看来挺有保暖功能,头发乱蓬蓬的,泛着银白色的油光,枣核般的眼睛深陷下去,配合着老树纹路般的皱纹愈发显示其“老朽”的地位,鼻梁高高的,嘴唇却像被刀削过一般的薄。
他的目光也落到了我的身上,带着好奇和猜疑:“哪儿来的?”
我和他目光交接,心中不免没有底气,随口说了个地名。
没想到他竟然会意一笑,说自己也是那儿的,原来我们是同乡。我心虚地低下了头,接连应道,老头又问:“离家出走啊?”
“体验生活。”我又瞎掰。
“唔……有远见,哪像那些不知民间疾苦的艺术家。”老头点点头,突然笑道,“也哪像我,体验了半辈子生活还没来得及享福,又被赶出来继续体验。”
“您……?”
“儿子不争气,有了媳妇忘了爹,联手把唯一的爹赶出来咯。”老头望向远方嘲讽地笑,有那么一瞬间我像是看到了父亲,那一模一样的悲伤的神情。
“这样啊……”我不知如何接话,老头继而说:“年轻人,会唱小曲儿吗?”
我点点头。
“那来一段儿。”
我擦了擦搁在一旁的吉他,闭上眼睛开始弹唱我最爱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一曲唱毕,我睁开眼,发现周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他们个个都好奇地看过来,有人惊叹有人怜悯,地上不知为何出现了许多硬币和小面额纸币,我连声道:“谢谢,谢谢。”
老头又踹了我一脚,说:“谢什么?还不继续唱。”
我吞了口唾沫,强忍住内心的狂喜和紧张,继续唱了起来。
一天之内,似乎全城都知道了我这“流浪歌手”的存在。过了好几天,钱币蜂涌而至。老头和我都很高兴,这意味着我们接下来能吃上些好东西。正当我入迷地唱着时,老头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穿过厚厚的人群没命似的跑了起来,我望着越来越陌生的街道,气喘吁吁,心想这老头是不是神经病。
到了一个偏僻的街区,老头喘着气说:“刚才城管来了。”
“不是吧!”也太倒霉了。
“这意味着你不能再唱了。”他神色有些黯淡,转瞬又恢复原状。
“为什么?”我纳闷,这城管真他妈是太平洋警察——管得太宽了!
“要交钱的,”他淡淡地说,“我们没那钱。”
“怎、怎么没钱了?”
“大家贪一时新鲜才给钱,过了这趟一分钱都不给。”老头一针见血地道出这现实,我一下子就从天堂跌到谷底。
我们灰溜溜地回到天桥底下,老头一直不肯用那笔钱,坚持带我扒垃圾桶、收集瓶子和大小八卦,我们为此争吵了好多次,但每次都没个结果。我也只有在闲暇时间哼个小曲儿来娱乐自己和老头,根本不敢大动干戈地拿起吉他引吭高歌,这时候也会引来几个听众,只不过没有之前声势浩大罢了。
可接连几天,我都看见个人鬼鬼祟祟地在我唱歌时候走来走去。他年龄和我相仿,高高瘦瘦的,像一根撑衣杆,时常穿着过大的白衬衫和灰不拉叽的长裤,面容倒是很清秀,可惜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浑然天成的泥土味道。
有一次我问快要睡着的老头:“那人是城管吗?”
老头顿时醒了:“你见过长一脸好人样的城管?”
我顿悟:“我错了。”
接下来这几天,由于我和老头忙着扒垃圾桶,没闲工夫唱歌,那哥们忍不住了,有次走过来特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说:“那啥,你好,我……我叫三芽,我很喜欢你的歌……能不能给我唱一段儿?我、我会给钱的!”
我看着他羞涩的表情,听着浓重的地方乡音,一瞬间热血沸腾:“好,我给你唱!不用钱!”
于是他紧挨着我坐下来,静静地听我唱完了一曲又一曲。
事后,他问:“那什么,你能给我签个名吗?我从来没听过明星唱歌。”
我汗颜,最后想了想在他的本子上写了“二货”两字。
三芽和我迅速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的那种。每天傍晚他都准时过来,捎上一块饼或一个馒头,毫不嫌弃地坐在我旁边,听我抒发离家的感想和音乐的梦想,以及对大山的渴望。他一言不发,面容却极为柔和,每次都仿佛有夕阳的暖光映在他的脸上,让人无端端地感觉到来自泥土的宁静柔软。
我说:“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平原,你知道山在哪儿吗?”
三芽随便指了个方向:“那儿。”
“啊?”我踮起脚尖站起来向远处眺望,却什么也看不到,低矮的楼房聚集在一起早就把这个小城与大山隔绝开来。
“你个二货,城外面到处都是山。”老头忍不住插嘴。
“来我家吧。”三芽也站起来,“周末我会回去。”
我看着他如星光般璀璨明亮的眼睛,笑着点头。
随即,他也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
周末,路上行人渐多起来。
三芽是在周六的早晨叫我起床的,在朦胧的雾气中他仿佛卷着暮色而来,带着泥土味道的光,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背上吉他随他而去,幸好没忘给老头留下我的真实姓名和地址。汽车一路颠簸,我浑身上下散发的臭味被人争相白眼,自始至终只有三芽一个人给我好眼色,静静地坐在我旁边,不说话,我知道他的眼睛里是大自然赐予的纯朴与善良,毫无恶意。
到达村里时,我像孩子一般急匆匆地跑下车。我第一次站在真正的泥土地上,置身于大山围绕的小小村落,心中的喜悦快要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出——那苍翠的树木扎根于于山坡,白云飘浮着与山顶作伴,田间有农民在干活,鸟儿盘旋着飞往屋檐,慢慢的绿意充盈了我的视野,几乎催人泪下。
我想,我的白日梦实现了。
三芽却打断了我的遐想,拉着我的手迅速跑去他家。
他说:“我爸妈现在都下地干活,我带你去收拾收拾。”
于是乎我连他家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被塞了衣服和毛巾到简陋的洗澡房里,我打量一下红砖和黄土组成的小屋,三下五除二洗了我出走这么多天来的第一次澡。
洗完澡后我走到三芽面前,被他震惊的眼神逼得说不出话。
“……怎么了?”我问。
“你……绝对会成为大明星!”他笃定地说。
我心中窃喜:“到时候给你签名!”
“我已经有了。”他笑着摇了摇手中的本子,上面是歪歪扭扭的“二货”。
我想,以后签的一定是真名。
接下来他带我逛了他从小去砍柴的山,和小伙伴玩耍的小山丘,以及他们家远处的红薯田,遥远的河边。一路上不是绿色就是绿色,我们沿着田垄追逐蝴蝶,摘了野花插在胸前的口袋,尾随老母猪走路一摇一摆,赤了脚在河边的小沙滩上聊天。
三芽问:“好玩吗?”
我说:“好玩。”
他却黯然地低下头:“好玩也得走,在这里呆着始终不是办法。”
我大惊:“为什么?”这里明明那么好!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哪像我家工业废气一吸一大把!
“这里……应该说,不能实现我的梦想吧。”
“梦想?”
“嗯,我想把爸妈接到城里,过好日子。”他笑着说,不知为何我却从他的笑容里看到某些悲伤的东西。
“可是……”
“可是什么?”
“我……我舍不得这里,”他笑中带泪,“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怎么会舍得大山呢?”
随着他的目光,我看到连绵起伏的山丘在风的吹拂下仿佛在轻微地叹息,树木摇摆着枝桠,溪水潺潺流淌,像在为三芽低声哭泣。
“你一定是属于这里的。”我望着他低垂的眉眼认真地说,“看,他们都在挽留你呢。”
晚上我躲在他的房间,胡乱吃了点东西就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撕了他的一页纸开始涂鸦,竟然写着写着就写出了几句歌词,最后忍不住拨起琴弦开始试着唱起来。“逃避晦涩难懂的文言,屏住呼吸隔离浓烟,我的空气是你的离言,你的向往是我的讨厌……”
睁开双眼时,我这才发现屋里站了五个人,分别是三芽、三芽的爸妈、弟弟和妹妹,我不好意思地站起身:“叔叔阿姨,你们好。”只见他们一脸阴沉,犹如暴风雨的前兆,三芽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一时间一个鸡毛掸子直戳我的脊梁骨,将我往外推去,阿姨操着我听不懂的方言一路打一路骂,我双手捂着头灰溜溜地被赶出大院,一时院里鸡飞狗跳好不安宁,远处的山林也发出哀伤的叹息。
最后我抬头看到三芽泛着泪光的脸颊,在心里小声说“再见”。
没有了三芽的陪伴我只能以卖艺度日,一路走一路唱,白天山里回荡着我赞颂它的歌谣,晚上星星与我作伴,置身其中的感觉说起来也不寂寞。然后我走回了小城,开始做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扫大街、洗碗筷、端盘子……样样我都抢着干,只因为我实现了自己到山里走一趟的愿望。白天我努力干活,晚上到城里唯一的酒吧唱歌,唱多了出场费也高了,可我依旧一无所有。
我离开了这座小城。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现在距离离家出走那一天是9年364天,我已经成为了业界
公认的成功音乐人。
傍晚下班回到家,我望着这件装修雅致却空荡荡的房子,心中感慨万千。然而还没来得及抒发感想,门铃突然被按响,打开门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面容清秀,不过有了小细纹,隔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眼睛仍清澈明亮,依然高高瘦瘦,像撑衣杆,浑身上下散发着我到现在还喜欢的泥土味儿。
“三芽!”我又是惊喜又是激动,握住他的手摇了几摇,差点不肯放开。
他仍是一如既往的羞涩和腼腆:“张屿先生……”
“别这么客气,我还是‘二货’!”我把他迎进门,马上泡茶招待。
他坐下来端详这房子,因紧张而绷紧的脸在暖黄的灯光下柔和了许多,接过茶便咧嘴一笑,露出洁白依旧的牙齿,说:“差不多十年了……”
“是啊。”我也微笑,看三芽也是穿着一身黑西装打着考究的领带,脸上刻着我所熟悉的疲惫,眼角泛着小细纹,我便知道这样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他所希望的吧。
“过得怎么样?”我问。
“还行。”他笑容依旧,却有些泛苦,“买了房子,结了婚,有了孩子,把父母接了过来,生活得井井有条吧。”
“这不挺好的吗?是你以前希望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倒有点怀念以前听你唱歌的日子了。”他低垂着眉眼,转瞬又抬起头,笑,这次是有点嘲讽的,“你的歌声,和我的大山……人真是贪心,抛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追求想要的,可是有了那东西后,又后悔自己为什么抛弃那最珍贵的。”
是怀念故乡了吧?以前那里的山山水水,清新空气,民风淳朴,到处都是好人好事活雷锋。可现在呢,上班下班家里家外,早就忙活得忘记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我望着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中,也忍不住感慨。
“我还不是一样。”我喝了口茶,嘴里弥漫着茶水苦涩的味道,滑下喉咙却感到一丝甘甜,想想我和这茶叶一样犯贱,离家出走痛苦的时候思念着家的甜,在家的时候却根本不知道它甜。
“现在还在离家出走?”他大惊。
“是啊。”我平淡地说。
“这么多年也没联系家里?”
“没。”
“和你爸和好吧,我那时还不是和他们和好了。”
我笑。
“怎么?”
“我在想,如果我当初就没离家出走,估计也混不成今天这人模狗样。”
“这倒也是……”
这天晚上我和三芽聊了很久,一次性说的话分散排布几乎能放置在十年里的每一天,后来他回家了,依旧带着笑容,说:“老婆孩子等我回去讲睡前故事。”
“去吧你!”我鄙视这欠扁的家伙,这不是在赤裸裸地讽刺我这单身汉生活嘛?
最后我望着这空荡荡的大房子,古朴宁静的家具,随意摆放的CD、书以及枣红色的抱枕,还有那从丽江某个客栈弄来的大大的落地灯,暖黄色的灯光洒落在每一个角落,也包括我的眼睛和我的心,我靠在沙发上,顿觉眼睛酸涩无比——为什么我刻意营造出来的家庭氛围,却还是这么冷?
模糊了的视线却被某个散放着某种光芒的东西吸引,那是我最喜欢的挂在墙上的钟,每天忠实地帮我记录了我出走这些年的时时刻刻,秒针一步又一步地、十分有规律地走动着,仿佛从前的我一步一步离开家又一步一步走近家,最终停留在家门外惶惶不敢入而等待着光阴的流逝。
54,55,56,57,58……59,60。
现在是离家9年365天整,也就是离家10年。
我强忍着泪水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爸,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