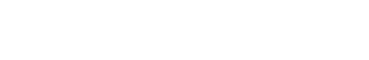岛礁
在冬天,想和世界有更多联系。
像是被长久的荒凉收留,想要更清晰地踩到脚下的实地,少一些梦游一般的午后,不再恼心于回忆白开水社交里的人是否真的存在。无数次幻想,想成为不那么离群的事物,成为蜂群的工蜂,过单线而清晰的一生。工蜂永远是快乐的,穷极一生去填满刻在基因的使命,永远因为基因密码的闪烁而愉悦。赫胥黎把这样的快乐写给人类社会,不寒而栗是因为人类缺失这段基因。族群繁衍的价值突变成个性价值,叫作进化。统一的价值向零落的主义进化,叫作文明。成为草丛的一份子,在合为“众”时最有价值。深深扎根于厚重的土地,风起时融进绿浪、与千万万个它不分彼此,等火焰逼近……
我总在神游。这个时代的病症是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和对后真相的麻木,林林总总,漂浮于世界的人在努力寻找低空飞行的法则。主义的共性是爱人类、抽象的人类,哲学家尤爱抽象的人类,于是对具体的人愈来愈淡漠。
遇见一个人,在午睡时喜欢给床帘留一条缝,看一道光透过纱帘晕染在墙上,她说像是在宁静中也保持一道与世界的联系。她喜欢一个人去电影院,享受和陌生人在一场电影里心照不宣的笑点,享受疏离礼貌的默契。她总是游刃有余地行走在这头,孤而不独。她爱浮世喧嚣,市井桥头的浮躁是她经过这儿的即兴剧场。我猜想她没见过更广义的世界,没路过生活的一地鸡毛,幸运地生于诗和梦的玻璃罩,聪明地与世界维持着审慎的距离。
她像最理性的局外人为自己设计感性的生活模式,浮于世事。我猜想这样的人会不会感受到“孤独”的情绪,是否也会期待一些莽撞的不期而遇。像是在懊恼地冒雨回家时被一把伞突兀地庇过头顶,侧头,不相熟的脸说,我们好像总是同路,一起撑着走吧。像是为了排解寂寞而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散步,红绿灯街口,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冒犯而自然地朝你讨支烟。我常常在想,与世界太过抽离的人是否希望着这样的“打扰”,是否期待这样意料之外的波澜来扰动他宁静到可怕的生活。
人总归是群居动物。与世界纠缠的人自不必多说,往往容易忽略的是,避世的人是最爱人类也最胆小的人,他把人类在想象中塑造成不得了的样子,当现实有所落差时,就轻易地瑟缩了。他可能有清高的灵魂、炽热的理想和天才的理性,但终归是不够勇敢的。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就不愿再拥抱生活。但还有一个真相是,没有谁能活成一座孤岛,没有谁能真正不渴望具体的人。拧巴的人,不如就别扭地把指头绕过身后,将自己与世界间打上一个死结,也好过迷路在雾中的岛。